教室后墙的挂钟指向六点十分,我正用美工刀削着新买的假发支架,课桌底下藏着明天漫展要用的兽耳道具。英语作业本突然从天而降,啪地砸在未完工的假发上——课代表林夏站在过道,马尾辫梢沾着走廊飘进来的桂花碎,浑身散发着薄荷味修正液的气息。
"最后通牒。"她指尖叩了叩我画满Q版草稿的课本,"下节自习课再交不上作业,老班说要请你家长来欣赏你的旷世cos大作。"我盯着她制服裙摆的褶皱,突然发现这挺像《蔷薇少女》里真红的裙撑造型,等回过神来,手里已经自动描完了三行选择题答案。
本以为这场闪电战天衣无缝,直到听见啪嗒一声。林夏的眼泪砸在作业本上,晕开了我刚写的"watermelon"里的字母t。她攥着皱巴巴的作业纸,声音像被踩碎的玻璃糖:"我改了两个晚自习的错题...你连题干都不看..."
消毒水味道的黄昏里,我头一次注意到她眼镜框上的猫咪贴纸,还有袖口洗得发白的蝴蝶结。那些精心准备的cos服突然变得轻飘飘的,压在书包里的兽耳硌得后背生疼。原来真正的角色扮演不在漫展摊位,而在某个课代表强忍哽咽的颤抖肩线里。
后来我用修补假发片的UV胶粘好了作业本,林夏戴着我的备用猫耳发箍在办公室背诵课文。班主任推门进来时,我们正对着窗户练习《黑执事》的经典台词。她泛红的眼角还沾着金粉,却已经能惟妙惟肖地模仿葬仪屋的诡异笑声——你看,有些眼泪会变成最特别的妆前乳。
现在想来,或许每个coser都要经历这样的觉醒时刻:当丙烯颜料在皮肤上开裂的瞬间,当道具剑柄沾上真实温度的时刻。我们笨拙地缝合着二次元与三次元的裂缝,就像林夏最终在我的运动服背后,用荧光笔画出完美对称的恶魔翅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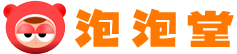 泡泡堂
泡泡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