摄影棚的补光灯还在发烫,我刚卸下精灵公主的尖耳朵道具,蕾丝裙摆就扫到了某本摊开的《吉米多维奇习题集》。抬眼撞见邻座男生推眼镜时镜片反出的冷光,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今年最魔幻的拍摄现场——我的假睫毛胶水还没干透,学霸君的微积分作业已经写到了第17题。
"要试试看吗?"他忽然把草稿纸往我这边推了推,碳素笔尖悬在洛必达法则的解题步骤上方。我发誓闻到了他卫衣上飘来的薄荷糖味道,混着化妆间残留的定妆喷雾气息,在四月潮湿的空气里发酵成某种令人心跳加速的催化剂。
事情要从三天前说起。为了赶漫展的舞台剧排练,我不得不把拍摄日程和小组作业打包处理。当缀满亮片的戏服和《复变函数》讲义同时在更衣室地毯上铺开时,来探班的表弟突然拽来个救兵:"这是我室友,能帮你搞定所有数学题。"
现在这位救兵正用建模竞赛获奖者的手,轻轻扶正我头顶摇摇欲坠的蝴蝶结发饰。指尖擦过发际线的瞬间,我听见他说:"其实三角函数和cos服褶皱弧度存在相似的美学逻辑。"这句话让我手抖得差点画歪了眼线,原来那些弯弯曲曲的积分符号,也能像裙摆的蕾丝花边一样拥有生命力。
拍摄间隙我们尝试过最疯狂的组合:他穿着我的备用lo裙研究傅里叶变换,我套着他的棒球服背诵台词。当暖光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写满公式的剧本背面,忽然觉得二次元和三次元的边界正在融化——就像他用口红在草稿纸上推导的方程,鲜红的等号划开两个世界的次元壁。
收工时发现他的围巾和我的choker缠成了死结,这场景倒像是某种行为艺术。他低头解结时碎发扫过我还没卸妆的脸颊,突然笑出声:"早知道该用拓扑学来分析饰品缠绕方式。"我摸着发烫的耳垂想,或许有些化学反应,比高数题更让人算不清答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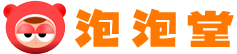 泡泡堂
泡泡堂